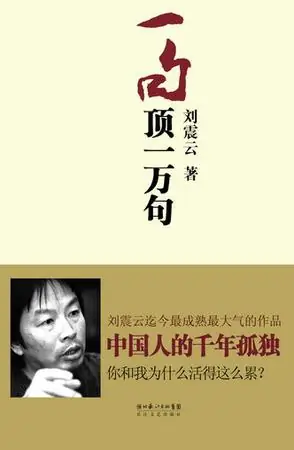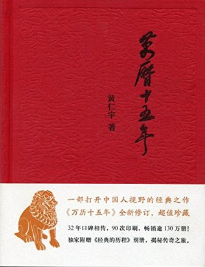文明诞生之初,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因为移民、入侵或占领等原因聚集在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同。法律是这些人结为一体的唯一纽带,尽管相关法律并没有完全得到所有头领的承认。这些混乱的人群,有着十分突出的群体特征。他们有短暂的团结,有英雄主义、易冲动、性情狂狷等群体特征。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是野蛮人。漫长的岁月是真正的造化者,种族就是它的作品。在环境长期一致、种族间不断通婚、一起共同生活等因素的作用下,不同的小群体慢慢融合成一个整体、一个种族,一个有着共同特征和感情的群体就此形成了,并且在遗传的作用下日益稳固。这群人变成了一个民族,渐渐有能力摆脱它的野蛮状态了。但是,只有在长期努力,经过不断重复的斗争以及无数次的反复,它才能获得某种理想之后,走出野蛮状态。
这个理想的性质并不十分重要,不管是崇拜罗马、雅典的强盛还是真主的胜利,都足以让一个种族中的每个人在感情和思想上形成完全的统一。在这个时候,一种包含着新制度、新信念和新艺术的新文明便诞生了。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种族会逐渐具备某些素质,某些建立丰功伟业不可缺少的素质。无须怀疑,它有时仍然是乌合之众,但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背后,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基础,即这个种族的秉性。种族的秉性支配着该种族狭小的范围内的机遇。时间在做完其创造性工作之后,便开始破坏的过程。不管是神还是人,全都无法逃出它的手掌。当某种文明强盛到一定的程度,复杂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止步不前。一旦止步不前,便注定走向衰落。
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它以种族支柱——理想——的衰弱为标志。基于理想建立起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动摇。随着种族的理想的消亡,种族团结、强盛的品质也会慢慢消失。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取代,并伴随着种族性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衰弱。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散沙。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在这个阶段,人们被个人利益和愿望搞得四分五裂,失去了治理的能力,即使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管理,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
随着种族的理想的消亡,种族团结、强盛的品质也会慢慢消失。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所取代,并伴随着种族性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衰弱。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散沙。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在这个阶段,人们被个人利益和愿望搞得四分五裂,失去了治理的能力,即使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管理,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随着古老理想的丧失,这个种族的才华也消失殆尽了。从此,这个种族的人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群体。他们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未来,只有乌合之众的短暂的特性。他们的文明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群众掌握至上的权力,野蛮风气盛行。文明也许依然辉煌,源远流长的历史赋予其华丽的外表,但这座岌岌可危的大厦早已被侵蚀,支撑不了多久,风暴一来,立刻就会崩塌。从野蛮到文明,一路追寻梦想,当这个梦想失去力量的时候,便开始衰落,最终走向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周期。
群体心理有着与“理性”个人完全不同的心理特征,而且群体不同,心理特征也不同。
这是因为,历史的所有事实无一例外地向我们证实,社会组织和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繁复庞杂,我们无权强迫社会组织在一夜之间突然完成深远变革。
所有历史事件无一例外地告诉我们,若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基础失去力量,无意识的野蛮群体最终会通过各种暴力革命手段迫使其解体或毁灭。
领导群体靠的不是纯粹的平等学说,而是情感。群体是情感的奴隶,只要找到能让他们动心的东西即可。
打算实施新税制的立法者会选择最公正的税收方式吗?不,对群体来说,最“不公正”的才是最好的。那些清楚易懂、负担小的税收制度,才是最容易被人们接受的。每天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儿税金,不会干扰群体的消费习惯,如此,征税就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倘若按薪资或其他任何收入的比例征税,让纳税人一次性缴一大笔钱,哪怕这种税制的负担比其他税制轻十倍,都会招致无数人的反对。立法者深知,数额较大的支出,容易刺激人们的金钱损失想象,所以新税收制度常常用难以察觉到的办法实行。而这种远见,正是群体缺乏的。
意识人格的消失和情感、思想向一个明确方向的转变,是即将形成有组织的群体的主要特征。
由于任何一种精神结构都包含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突变会让其中某些可能性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对待包括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件事情的态度上,智商再怎么杰出的人,也不见得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一个伟大数学家和鞋匠之间的智商可能有天壤之别,但就性格来说,他们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
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而这正是与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极为对立的情感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则很难产生这种情感倾向
群体是个无名氏,个人不必承担责任,如此以来约束着个人行为的责任感便消失了,他便会肆意妄为。
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群体意识里没有障碍一说,即使是有,那也是充满敌意的挑衅。
群体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视若无睹,他们永远只看到他们认为应该看到或者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这就意味着,群体惯于用歪曲性的想象力把这种由想象建立的幻觉与真实的事实混为一谈。
我们习惯于说童言无忌,哪怕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也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最爱撒谎。
当历史传承到需要记载下来的那一刻时,早已丧失了它的本来面貌,我们只能把史学著作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了作者对思考结果的解释。
各种事实都证明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极可能一句也没有。所有能够打动群众的,能够在群众范围内得以流传并保留下来的,只是这些伟人在神话中的形象。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伟人在神话中呈现的形象。我们要的是能打动我们心灵的神话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
群体的想象力会改变一切,不论这件事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正因为这样,历史才会背离它的真相,呈现出光怪陆离的面貌。
不幸的是,群体感情的夸张倾向,通常把人类的恶劣表现到极致。1527年5月6日夜,罗马被雇佣军占领,八千多名百姓被杀,但这只是开始。夜晚狂欢过后,极度激动的雇佣兵开始洗劫教堂,他们还洗劫教堂和要人的宫殿,闯进修道院强奸修女,残酷迫害百姓。
群体很容易干出恶劣、极端的勾当。这是原始人的本能遗传的残留,孤立的个人因为担心受罚,不得不约束自己
群体只是擅长把感情提升到极高或极低的境界。
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锋芒毕露、信誓旦旦。他们少不了要夸大其词,而且以不断重复、绝对不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演说家惯用的技巧。
他们并非是有所醒悟,因为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群体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群体随时会欺压软弱者,但对强权低声下气!
群体最终会回归保守,群体可能渴望通过改朝换代换取卑微的需求,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常常发动暴力革命,但却常常沿用旧制度,从中国王朝的更迭中便可看出端倪。这些旧制度本质反映出了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此专制者轻易便能拥有整个种族的顺从。
在生活中,有的人因为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本能,便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和这种破坏性本能,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正是十分懦弱的残忍。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群体为了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可以英勇地面对死亡。
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都算作美德的话,那么毋庸置疑,群体最具备这些美德,而且他们达到的水平,哪怕是德行最高尚的哲学家也望尘莫及。
只有简单而明了的观念,才能被群体接受,但并不是所有观念都是简单明了的,因此必须经过一番彻底改造,使之变得通俗易懂,才能被平庸的大众接受。那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或科学观念,群体自卑心理导致的智力水平根本无法理解,更别谈接受了。因此,对它们的改造必须更加彻底。种族间理性程度和聪明才智都不同,因此这种改造有时大一些,有时小一些,但都必须向低俗化和简单化改造。
群体推理只是把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会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不妨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而且也绝不会受到推理过程的影响。
凡是和群体有密切交往的演说家,无一不擅长建立对群体有诱惑力的形象。任何一个人做到这一点,便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是20本富有真知灼见的著作,也不如几句有感召力的话语更能说服群众。
有些意见轻而易举就得到普遍认同,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能力根据推理形成自己的独特看法。
表象总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群体无视现实,无论是亲眼所见,还是逻辑严谨的劝告,群体都不为所动。那些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就能对群体产生巨大的影响。
想领导群体,就得在他们的想象上下功夫。几乎所有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都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上的。
究竟如何影响群众想象力呢?只需要注意一点,不可求助于智力和推理,这也就是说,绝对不能够采用论证的方式。
2025.04.09 星期三 晚21:00
假如我们对群体的这些特点做更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政治大动荡的时代,都有同样的感情和古怪的形式——没有比宗教感情更好的称呼了,这就是偶像崇拜。
偏执与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侣。
无论时代进步到何种程度,即使不再有圣坛与雕像存在,也会有新的形式来替代。
只有经验这位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指出我们的错误——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劳动的事业。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教科书,不可能提高我们的智力水平。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而这些优良品质,偏偏不是死读书就能得来的。
思想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因此,我们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建筑工地和医院等地方,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只有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得到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地产生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采用的方法也糟糕透顶,以至于已经成为一种严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过多地延长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培养懒汉的寄宿制度,过多的人为训练、教学和功课,对今后的时代完全没有考虑,对人的职业缺乏安排,对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装聋作哑,不考虑学生如何适应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教学生如何保持坚强意志……
有必要的准备、最重要的学习、丰富的常识、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凡是年轻人应该拥有的知识,我们的学校一样也没有教。我们的教育不但没有让他们获得更好的生存能力,反而破坏了这些能力。这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一走入社会,进入他的活动领域,就开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与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甚至让他失去生活能力。这样的教育制度,对年轻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有难以恢复的可能。学校的幻想与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地破灭了,强烈的欺骗感、失望感,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完备的青年人难以承受的。
如果想要让群众相信什么,就先得搞清楚让他们兴奋的感情,再假装自己也有这种感情,必要时还得用极端的行为表现对这些感情的狂热。再打一套低级组合拳,用一些非常富有暗示性的概念改变他们的看法。如捏造场景、追忆往昔、憧憬未来等,这样才能够引导大众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慢慢揭开激起某种感情的目的。
人和动物一样,有模仿的本能。这是必然的,因为模仿总是比创造容易。正是这种模仿,使得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还是服装,有多少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支配大众的是榜样,不是论证
包括意志在内的一切事物都会屈服于衰老
不存在任何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其最终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都存在着极端分歧,并且使大众对于一切和他们没有直接利益的事情都漠不关心。
从众行为导致我们服从别人的怂恿
无论是天才还是智障,只要一受大众领袖的影响,就变成了被无意识情绪支配的生物。
要求一个善于思考的团体就某个并非技术性的问题发表意见时,智力就起不了多少作用。
群体的权力令人生畏,然而身份团体的权力更让人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