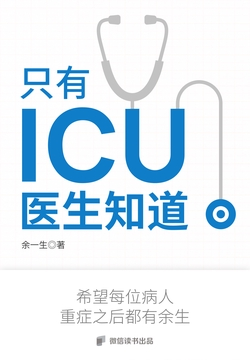《只有ICU医生知道》
《只有ICU医生知道》
于是我告诉她,想当小学老师,你可能得有本科,甚至硕士的文凭。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得自己去争取。而我作为妈妈,也有自己的梦想要去实现。
做你想成为的大人吧,无论你是那个孩子,还是那个家长。
一朵“花”可以慢慢地开,甚至可以开得和其他花都不一样,这并不代表它会不美丽。
她清楚地记得父母对其他姐妹的爱,却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我不知道她是否清楚,自己将要面临怎样的人生。
“你不懂,那种孤独的感觉,一天都没个人说话。”
每当我和他们聊起大梦的病时,他们从来不会像普通家属那样问我,这个病能不能根治,能活多久,预后怎么办?她的父母唯一的要求,是珍惜现在。
线粒体和细胞是共生的关系,它提供能量,细胞提供适应它生存的环境。但是,线粒体并不像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脱离细胞就会孤单地死去。
理论上来说,在一个很严苛的,和细胞相近的环境里,它也能够生存,继而独立完成自己的功能。
我甚至和晓兰的儿子一样去算过命,希望上天多给我一点时间和妈妈相处。
她每天躺在那张小小的病床上,说她想她的妈妈了。
因为直到今天,我也还在这样的痛苦里挣扎。工作了十几年,我还没有完全明白,对于注定会离开的人来说,如果来到ICU结局注定是死亡,我们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有时我值班,会碰到老太太一个人跪在角落里,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地祈祷。也许是来医院里的人,心里都装着更重要的事,来来往往的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老太太。
那时我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帮助晓东顺利戒掉药瘾,成功出院。直到一年后,我又遇到一个病人,给了我答案。
当我们的身体习惯于依赖什么,就会逐渐失去独立生存的能力。何娟习惯了呼吸机帮她喘气,而她自己用于呼吸的肌肉,就会慢慢失去力量,甚至萎缩,这叫作ICU获得性肌无力,在长期使用呼吸机的病人中很常见。
三个多月过去,每一封手写信都被戴阿姨仔细地整理起来,放在何娟的床头柜上,现在已经是厚厚一沓。
她脸色红润了很多,脖子上气管切开的疤痕几乎看不见了。我知道,她的生活终于要脱离ICU,大步向前迈了。
我是在工作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四个字(情暖人心)有多重要,它可能本身就是一服很好的“药”。
但我想,无论是医生,还是病患都该有挣脱惯性的勇气。
作为一个ICU医生,很多人在遇到我以前,过的就是那种最普通的人生,上学、考试、上班、结婚,每天纠结下一顿吃啥,也每天思考人生是旷野还是轨道。但很难说,命运在哪一刻就把人推向了转折点,推到了ICU医生面前。
我曾经觉得把病人救活,就很了不起了。但一个又一个病人让我意识到,活下来之后的人生,也无比重要。
到时候她也要当经纪人,签10多个主播,但阿紫说:“我当了经纪人,不会这么冷冰冰的。”
我却默默记下了几个关键词:瘦小,被欺负,健身房。
我想起小孙醒来以后,姐姐来探视他。小孙管病房里的医生、护士都叫“姐姐”,管自己的亲姐姐却直呼其名。姐弟俩隔了太久没说过话,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些尴尬。
那一刻,我有点读懂了这个少年的自尊。
我们都曾想成为另一个人,试图改变外表,觉得只要这样,人生就会好起来
我曾误以为,外貌会决定很多东西。比如爱情、事业、被多少人喜爱、是否拥有完美的人生。但现在我觉得,自己成为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比长成什么样,重要得多。
每次都要面对一个我回答不了的问题:为什么人会死?
我想投诉的是这个制度,为什么病人都是重症了,医院还是没有特效药物?”“为什么人都可以在火星生活了,一个红斑狼疮治愈不了呢?”
我没有插话,心里默默感慨,生活已经如此苦了,宋小鱼想喝点甜的,说不定意味着,她可能也想好好生活了。
每一个人都尽力了,每一个人都好辛苦,好绝望。而我们做的,就是帮这一家人重新注入希望,哪怕只能撬动一个人,让她用新的视角看待这一切,这个家都有可能重新运转
也许终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生命巨大的失去,病痛和死亡。而宋小鱼一家,还有许许多多带病生活的家庭,都在不断地教我,如何去面对这一天?一个45岁得了红斑狼疮的女性告诉我,她现在把做透析,就当作做SPA。她刚生病的时候,很怕成为家里的拖累,但老公和孩子表达关心的同时,依然照常打工、上学,她的家人用实际行动告诉她,这没什么。后来我每次见她,她都捧着手机,一边笑呵呵地追剧,一边躺在床上做透析。
告别时,他说,“问题总会慢慢解决的,解决不了的问题,急也没有用。”
不知道是说给我们,还是说给他妈妈。我站在一旁,看到他妈妈搂着他的手,好像又紧了紧。
我唯一不能接受的,是病人自己放弃。作为医生,哪怕病人放弃,我也要全力以赴。我不是一个会轻易动感情的人,写下这段经历的时候,可能是我流露感性最多的一次。记录了那么多ICU的故事,我总会倾向于记录那种,奇迹中生还的病人。我觉得这样的故事能告诉想要放弃的人:“人类,一定要记住,你的生命力超过你想象。”这句话不只对在病人说,对在人生道路上行走的你我,也是一样的
当父母在子女身上寄托了太多期待,孩子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至于他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似乎都成了无所谓的事情。
3岁的儿子总是问她:“妈妈,我可以哭吗?”她说你可以哭。儿子要出去玩,她说你要玩得开心哦,儿子问:“那我可以玩得不开心吗?”她想了想回答,当然可以,因为不开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状态,有不开心的时候,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开心。这样的对话多了,当她问自己儿子,可以不可以的时候。她的儿子总是回答她:“可以。”是啊,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呢?
而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歌叫《大梦》。它唱了一个人平凡普通的一生。读书、离家、工作、结婚、生子、老去。故事里的女孩也叫大梦。但我想,这样平凡普通的一生,可能是对他们最美好的祝愿。
在此之前的学生时代,我很少思考过这个问题:人类攻克一种疾病到底需要多少年?我以为那堆在一起比我人还高的教科书,早已写好了所有答案。当我真正成为一名医生以后,我才发现原来医学给我们留了这么多未解的难题。
因为线粒体的问题,她的身体缺乏足够的能量,去分解过多的乳酸,那些年轻人喜欢的徒步、剧本杀对她来说都是可能危及生命的事情。同时,她必须保持情绪的平静,任何一点情绪波动,都会使耗氧量增加。而她的线粒体也无法提供这么多能量,于是无氧代谢增加,身体开始分泌乳酸。
画面里,楼梯间一如既往的昏暗,角落里还有偷偷抽烟的家属留下的烟头和垃圾。老太太穿着件过时的衬衫,一头白发在脑后盘了个极小的髻,她跪在楼梯拐弯处的最角落,低着头,闭着眼睛,双手合十,嘴里碎碎念着,然后慢慢弯下腰,许久没有起来。